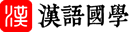射以觀德-文苑

智者善喻。論及理想,揚(yáng)雄喻之以射:“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后發(fā),發(fā)必中矣。”確為至論。
禮、樂、射、御、書、數(shù),射為六藝之一。在古代,射并非射箭御敵這樣簡(jiǎn)單,它由功用而形而上到修身的高度。孔子說(shuō):“君子無(wú)所爭(zhēng),必也射乎。”雖然君子之爭(zhēng)在射,但更在“禮”,揖讓而上場(chǎng),互禮而下場(chǎng),然后登堂喝酒。習(xí)射與修養(yǎng)密不可分。
哲學(xué)家王陽(yáng)明對(duì)于“射”,更有超拔的論述:“君子之于射也,內(nèi)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志”與“體”,身正與志端,理想與“標(biāo)的”,在古人“射”的范疇里,是表里相生、虛實(shí)相對(duì)的。為了論述他的觀點(diǎn),王氏將修德與習(xí)射進(jìn)行了對(duì)比,認(rèn)為它們皆發(fā)自于心。心躁,則德必淺,體必斜,視必渙散,氣必餒,色必驕矜。一個(gè)身斜走神氣餒驕傲的人,能射中是極為意外的;如果相反,心端然,則體必正,容必肅,氣必舒,視必專注,具備這些,射不中是極為意外的。
射之內(nèi)涵其實(shí)在“德”,在心。楊雄以射道喻人生理想,要說(shuō)明的亦為射向理想靶的看似道路萬(wàn)千,其實(shí)發(fā)乎心,發(fā)乎德。修身、矯思,都是要通向“立義”修德。修身,必修向義;矯思,必矯向義。人生的目標(biāo)必須為“德”之所肯,修養(yǎng)必須唯德是從,思想必須以德涵養(yǎng)。心正,德厚,目標(biāo)光明,則“體”必正,“容”必肅,“氣”必舒,“視”必專注,則必能射得正,射得遠(yuǎn),必能“勝而不張、負(fù)而不馳”,必能持久。德的重要由此可見。
德與才孰輕孰重,自古就有論辯,但歷史證明,德比才更重要。因?yàn)榈聸Q定著箭矢的目標(biāo),決定著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方式。德才兼?zhèn)渲^之圣,如果不能盡善盡美,則必選擇德。德厚,則目標(biāo)必不害己,必不害人。智伯無(wú)德,導(dǎo)致三家分晉,司馬光在論及此事時(shí)認(rèn)為這是“才勝德”的結(jié)果。有才而無(wú)德,禍人害己,南朝宋廢帝劉昱是典型代表,他天才絕艷,“凡諸鄙事,過(guò)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zhí)管便韻”。但是他“天性好殺”,喜歡箭射大臣肚臍,十五歲便人死國(guó)滅。
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方式有多種,德為正途。神童蔡伯俙三周歲即為太子伴讀,才不可謂不高,路徑不可謂不捷,但他選擇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方式卻令他最終射不遠(yuǎn)。皇宮門檻高,每出門,蔡伯俙弓身以為橋,以便太子。太子登基,卻取另一個(gè)神童伴讀晏殊為相,原因是治理國(guó)家,“無(wú)真才不興”,其實(shí)更有言外之意:德之不修。
修德與靶的相輔相成。若廢帝劉昱自小的教育得當(dāng),他的目標(biāo)必然不會(huì)是大臣的肚臍;若他自小的目標(biāo)不是“好殺,一日無(wú)事,輒慘慘不樂”,那么他必會(huì)修德。錢學(xué)森拋卻厚祿一心回國(guó),是德的加持;某青年大肆宣稱國(guó)外空氣香甜,不辭長(zhǎng)做他國(guó)人,是德之缺失。
“德才”的選擇往往令人糾結(jié),尤其是為人父母教育子女之時(shí),往往因?yàn)楦捎^、更直接的“唯財(cái)是舉”“唯貴是舉”,而忽略德的涵養(yǎng)和引領(lǐng),卻不知道人生的大弓必須以德修養(yǎng)才能正,人生的內(nèi)核必須有“德驅(qū)動(dòng)器”才能自正自新,人生的目標(biāo)必須在德的涵養(yǎng)下、指引下,才能有光明的屬性。人生目標(biāo)之實(shí)現(xiàn),譬如六藝之射,矯思修身,射以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