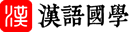被壓抑的過去終將作祟于現在-文明

二戰結束之后,在荷蘭與德國交界處豎著這樣一處標識:“此地乃文明世界之盡頭。”的確,那時的歐洲已淪為野蠻大陸。在戰爭的摧毀性打擊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秩序、法律甚至道德在不少地方早已蕩然無存,是非對錯失去意義,人們為了生存無所不用其極,在廢墟中用暴力爭搶著最后幾塊能填飽肚子的馬鈴薯——這景象很難讓人相信竟會發生在20世紀的歐洲。在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中,唯一尚能令人欣慰的一點是:無論如何,這場可怕的戰爭總算結束了,盡管是以如此可怕的方式,但它終于結束了。
就像現在也有很多人警告核戰爭會帶來極端可怕的結果一樣,這一悲慘的境地并不是沒有人預見過。雷蒙·阿隆曾把1914—1945年這個連續時段稱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但1890年老毛奇便曾嚴肅警告,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將極為可怕,“其延續以及結束的時間是無法預計的,可能是七年戰爭,也可能成為三十年戰爭”。更早一些,恩格斯在1887年就預言,德國必將卷入破壞程度極大的世界大戰,可預期的結果是:“三十年戰爭造成的破壞將會縮短到三至四年,戰爭將遍及整個大陸,饑荒、瘟疫……軍隊及人民普遍變得野蠻,我們的貿易往來將出現無可救藥的混亂,工業與信貸最終都普遍破產,古老國家將崩潰……簡直不可能預計這一切將會怎樣結束,誰將是戰爭的勝利者。”他說對了,但先知的悲劇在于:他們往往要到事后才被證明預言得多么正確。
何謂“野蠻”?我想就是人在極端處境下拋棄那些較高的精神需求、道德、禮節(它們又不能當飯吃),只不顧一切地緊緊抓住最基本、最原始的生理需求(按馬斯洛理論來說,就是只剩最底下的一層),而這些在正常的日子里,是會讓自己感到羞恥和厭惡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里莫·萊維曾說過,為了生存、思考和工作,當時他已培養了一種“古怪的無情”:“希望和無助的快速輪替,足以毀滅任何正常人。我們不正常,因為我們饑餓。那種饑餓和普通人錯過一餐但會有下一餐的感覺完全不一樣。那是一種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們的行動。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遠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遠的,才是對家庭的回憶和對死亡的恐懼。”
雖然讀來觸目驚心,但這并不可笑,吊詭的是:也正是看起來“野蠻”而極端的求生意志,才使得“文明”能挺過戰爭可怕的打擊從而延續下來,因為如果人類在肉體上被整體消滅,那也就談不上文明的延續了。那時的西歐文明,的確算得上是命懸一線,民眾是如此渴望那些最低的需求:食物、安全和基本保障,以至于別的都無暇顧及。1947年初,駐西德的美國占領軍副司令盧修斯·克雷說:“在每天1500卡路里的共產主義者和每天1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間,選擇是顯而易見的。”
“戰爭就是地獄”的訓誡,之前并不是沒人說過,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發展到如此慘烈的程度。因為現代的全面戰爭要求國家投入所有資源來贏得戰爭,這也就意味著要徹底摧毀并榨干對手最后的一點力量,才能迫使它無條件投降。在戰爭中竭力主張擴大對德轟炸的英國空軍司令亞瑟·哈里斯曾坦言,轟炸造成的平民傷亡并不是不小心造成的“附帶損害”,相反,“本來就是我們轟炸行動的目的”。“平民目標”和“軍事目標”的區分其實經常是十分模糊的,就像英國的漁船和游艇會被征用來運送戰士和軍事物資、蘇聯的拖拉機廠被改成坦克廠一樣,任何一個平民也可能是敵人力量的組成部分——考慮到納粹曾讓1800萬德國人(約占德國男性的一半)穿上軍裝,這么說不算夸張。
正因為如此,在戰后的歐洲,棘手的一點在于:幾乎各方都有自己的“創傷性體驗”,加害者也可能變成受害者,受害者在得到機會時又會迅速復仇而變身為加害者。各國都建構起自己在戰爭中所受不公的神話,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基思·羅威在《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中所說:“真相是,戰爭造成的道德困境誰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體、所有政治信念,盡管有著天壤之別,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雙重身份。”只有在德國人和猶太人中,討論這些問題是禁忌。然而在戰爭結束50多年后,關于德國是戰爭受害者的議題仍一度成為德國社會的焦點——關于當時德國城市遭受到的針對性轟炸、關于戰后被強制遷移的1500萬德國人,以及盟軍在德國的種種暴行,以至于出現了某種“受害者崇拜”。其實,每個參戰國都不缺這種記憶,就像日本也會突出自己受原子彈轟炸的受害者一面,而極力淡化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加害者形象。德國人令人可敬之處也在于此:他們并未沉浸在“我也是戰爭受害者”的自憐中,而是迅速有人站出來批評“這種新出現的把德國看作受害者的危險傾向”(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希·韋勒語),更不用說德國所受的磨難并不能抵消它在猶太人大屠殺中所犯下的罪孽。
因此,人們不僅在那些年里在戰場上廝殺,在戰爭結束之后,仍在歷史敘述和記憶上撕扯。托尼·朱特在《戰后歐洲史》中曾說:“內戰的創傷性特征之一是,敵人即使被打敗,但他還在;只要他在,沖突的記憶就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二戰的歐洲戰場,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場至今未消散的歐洲內戰。彼此不相容的記憶、無法妥協的敘述,足以使歷史學家成為一個令人感到既豐富又痛苦的職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是有史以來被談論得最多的一次戰爭,有關它的書籍、資料早已多到窮盡一個人的一生也看不完的地步。它繼續充斥在書店、媒體版面、熒幕上,在這里,歷史并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動成為歷史,它是活生生的當下的一部分,并繼續攪擾著現在。
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都曾說過,被壓抑的過去終將會作祟于現在。的確,如果沒有現實中的和解,那人們只會記住那些有毒的歷史或對自己有利的記憶,而正如基思·羅威所言:“試圖忘記過去只會引起憤恨,最終引起對事實的危險歪曲。歪曲事實比事實本身要危險得多。”100多年前,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說得明白:“我們把什么作為未來的目標,取決于對往昔的意義的制定。”從這一點上說,現在之所以能夠這樣坦率地談論那段令人難堪的歷史,是因為如今已有了一個決心走出這一歷史困境的全新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