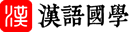尋找“失去的”居住-人與社會(huì)

和所有那些告別福利制度的行業(yè)一樣,如今住宅產(chǎn)業(yè)甚至已經(jīng)成為最時(shí)髦的行業(yè),它比其他行業(yè)更徹底地皈依了市場(chǎng)原則。比起五六十年代那個(gè)住宅緊缺時(shí)代,我們對(duì)自己居住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選擇,對(duì)根植于內(nèi)心的對(duì)居住環(huán)境和品質(zhì)最隱秘的欲望有了更多的釋放渠道。然而盡管有越來(lái)越多的人加入到對(duì)房子的設(shè)計(jì)和生產(chǎn)之中,也還有越來(lái)越多的人陷入到對(duì)“天人合一”、溫情脈脈的既往居住方式無(wú)限的追憶里去。人們開(kāi)始反思這場(chǎng)60年來(lái)快樂(lè)與痛苦交織的居住變遷史:是居住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居住?
被規(guī)制的居住
趙景昭在四合院住了兩年后,1959年,搬進(jìn)了同樣是他父親從郵政系統(tǒng)分得的一套住房,在北京三里屯附近。這種被稱(chēng)為“二型住宅”的單元房是趙景昭后來(lái)所供職的北京建筑設(shè)計(jì)院設(shè)計(jì)的第一批住宅通用圖,也曾是很多早期享受福利分房的人共同的記憶符號(hào)。
某種意義上,中國(guó)人正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開(kāi)始了住宅的標(biāo)準(zhǔn)化時(shí)代。“標(biāo)準(zhǔn)化”的一層含義是替代傳統(tǒng)建筑方式的“工業(yè)化”批量生產(chǎn)模式,它意味著新的技術(shù)——對(duì)于向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中國(guó),這當(dāng)然令政府和人民興奮。而對(duì)多數(shù)人而言,更為真實(shí)的含義還是另外兩個(gè)方面,趙景昭說(shuō):“一是中國(guó)人將在未來(lái)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注定要面臨住房的緊缺和擁擠時(shí)代,因?yàn)?lsquo;工業(yè)化’的出現(xiàn)也是人口劇增和住宅需求量急增下的應(yīng)對(duì),二是,當(dāng)中國(guó)人享受著只需微薄付出就可獲得一套福利分房的同時(shí),也將沒(méi)有任何個(gè)人選擇的余地,‘給你什么你就只有要什么’。”趙說(shuō),對(duì)于習(xí)慣于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形態(tài)下舒適和緩慢居住方式的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他們將不得不面對(duì)并承受理想和現(xiàn)實(shí)的居住尷尬。
對(duì)于剛剛搬出四合院的趙景昭來(lái)說(shuō),1959年的居住變遷是無(wú)比尷尬的。“所謂‘二型’住宅,那套圖紙是在蘇聯(lián)專(zhuān)家指導(dǎo)下設(shè)計(jì)的,當(dāng)時(shí)還沒(méi)有意識(shí)到人口壓力這個(gè)問(wèn)題,所以房型設(shè)計(jì)還是很大,單元平面一種為五開(kāi)間一梯二戶(hù),每戶(hù)3~4個(gè)居室,平均建筑面積是98。88平方米,另一種為一梯三戶(hù),每戶(hù)為兩個(gè)居室,平均面積是62。92平方米,我們家住的單元房是后一種類(lèi)型。”趙景昭說(shuō),“相比較后來(lái)的住宅,這相當(dāng)奢侈,設(shè)計(jì)總體來(lái)說(shuō)是很合理的。”“但國(guó)家計(jì)委1957年頒布的《住宅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的幾項(xiàng)規(guī)定》里寫(xiě)明,每戶(hù)的居住面積不得超過(guò)18平方米,這樣,62。92平方米的房子不可能允許只有我們一家人住在里面,必須要兩家合住一個(gè)單元。”
合用一個(gè)廁所在當(dāng)時(shí)的居住條件下是司空見(jiàn)慣的事,居住的私密性當(dāng)然就變成集體的敞開(kāi)性。趙景昭說(shuō),這種房子是四層磚混結(jié)構(gòu),蘇式密排木屋架坡頂,樓板為30厘米厚的預(yù)制混凝土方孔板,樓板和墻體都薄,隔音效果很不好,“隔壁有兩個(gè)小男孩,淘氣得不得了,三天兩頭哭鬧還不算,經(jīng)常用釘子在兩家共用的墻上敲一個(gè)洞,小孩子好奇心重,好想看看對(duì)家在干什么,我母親發(fā)現(xiàn)了,就拿面團(tuán)塞住,過(guò)兩天又被捅掉了,就再塞”。
“標(biāo)準(zhǔn)化”最直接的動(dòng)力是滿(mǎn)足解放后日益膨脹的人口與隨之膨脹的住房需求。北京建筑設(shè)計(jì)標(biāo)準(zhǔn)化辦公室主任林晨說(shuō),要在有限的空間安排下盡可能多的人。這樣的居住現(xiàn)實(shí)和居住的空間背景有點(diǎn)類(lèi)似解放前的上海——那種閑適生活其實(shí)在現(xiàn)代化面前變得特別脆弱,與北京相比較,上海其實(shí)早就形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集約化。
同樣是在1949年到北京參加工作的北京規(guī)劃局高級(jí)顧問(wèn)張敬淦1921年到1948年在上海的石庫(kù)門(mén)渡過(guò)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shí)代,“上海的租界被洋人和富人居住,普通老百姓都擠到了石庫(kù)門(mén)這些民居里,盡管那時(shí)整體上的人口遠(yuǎn)沒(méi)有達(dá)到后來(lái)的壓力,但這種人為的空間分割在事實(shí)上造成和后來(lái)其他城市因人口膨脹所形成的相似局面。”張敬淦親歷了上海老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時(shí)代,他說(shuō),“石庫(kù)門(mén)的老房子倒是很好找,一排從頭上第一家是1號(hào),排到20號(hào),就開(kāi)始叫20弄,每條弄里面至少要住二三十戶(hù)人家,多的要住上百戶(hù)人家,真是雞犬之聲相聞,每家的院子進(jìn)去有一個(gè)狹長(zhǎng)的小天井,也分正房和東西廂房,但空間利用率非常高。”張敬淦回憶,他們家正房后面是一個(gè)通向二樓的樓梯,在一樓半的地方有個(gè)朝北很窄很小的“亭子間”,一層和二層之間還有一個(gè)閣樓,就是在樓梯上開(kāi)個(gè)門(mén),后來(lái)加住進(jìn)來(lái)一戶(hù)人家,又在二層也搭了一個(gè)閣樓,“亭子間”的下面還開(kāi)了一個(gè)房間,“這些在原本現(xiàn)有空間下多隔出的空間甚至多的時(shí)候要有一家人住在里面,有的房間拿布簾隔開(kāi),分兩家住。”他說(shuō),“一家人所有的活動(dòng)都在一個(gè)房間里完成,根本沒(méi)有任何私密性可言,上廁所也在房間里,不過(guò)就是找一個(gè)隱蔽點(diǎn)的地方,拿布簾子遮一下。所以家與家之前的干擾也相當(dāng)大,張家吵架李家聽(tīng)得一清二楚,碰到關(guān)系差一點(diǎn)的院子,家庭私事很容易變成街談巷議四處傳播。龍骨鋪的地板本身就不隔音,加上空間被盡可能地縮小,樓上一點(diǎn)點(diǎn)走動(dòng)樓下聽(tīng)得清清楚楚。”張敬淦笑著說(shuō),這種居住狀況可能也是造成上海人斤斤計(jì)較的原因,“比如,樓梯間是黑間,要安燈泡,不是一個(gè)燈用電大家攤,而是一家一根電線一個(gè)燈,誰(shuí)家用開(kāi)誰(shuí)家的,用完了下樓再關(guān)掉,如果開(kāi)了別家的燈也是容易引起糾紛的”。“人多住房緊這種矛盾就很難避免”。
趙景昭說(shuō),1959年前后住宅建設(shè)時(shí)代的原則是“談適用,不談舒適”,要求“住得下,分得開(kāi)”,“這家人能住下了,如果這家有個(gè)女兒長(zhǎng)大了,要能分得開(kāi),所以當(dāng)時(shí)的房型以最緊湊的2室戶(hù)為主”。
這兩條原則也成為“工業(yè)化標(biāo)準(zhǔn)”里的“社會(huì)標(biāo)準(zhǔn)”被推諸廣之。“許多人的居住問(wèn)題得到了及時(shí)的滿(mǎn)足。”林晨說(shuō),但也相應(yīng)失去了中國(guó)人傳統(tǒng)居住中的很多“舒適性”因素,“‘標(biāo)準(zhǔn)化’強(qiáng)調(diào)減少‘構(gòu)件規(guī)格’,所以當(dāng)時(shí)的一批住宅只用了3。2米一種開(kāi)間,6米一種進(jìn)深,1959年根據(jù)北京總體規(guī)劃的每人居住面積9平方米的住宅指標(biāo),我們?cè)O(shè)計(jì)了八種住宅的平面方案,編制了39套組合體,大部分是四層磚混結(jié)構(gòu),比較流行的五開(kāi)間三戶(hù)主導(dǎo)了國(guó)內(nèi)住宅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設(shè)計(jì)格局,但這種以個(gè)人面積底線為前提的設(shè)計(jì)帶來(lái)的一個(gè)致命的問(wèn)題是中間單元沒(méi)有穿堂風(fēng),這恰恰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民居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被懷念的老房子
北京首席中式住宅“觀唐”的老板、清華紫光房地產(chǎn)開(kāi)發(fā)有限公司董事長(zhǎng)呂大龍說(shuō),“四合院一家住就叫豪宅,10家住就叫大雜院”。
照這樣來(lái)劃分,張敬淦出生時(shí)的老房子肯定屬于前者。他說(shuō)他關(guān)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居住的記憶都來(lái)自那里。張的祖上是杭州知府,在當(dāng)時(shí)的松江府(現(xiàn)在上海市的松江區(qū))置了一些田產(chǎn),蓋了幢大宅院,“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七開(kāi)間,十幾進(jìn)”。張敬淦說(shuō),在功能上和北京的大四合院基本相同,進(jìn)大門(mén)后便是第一道院子,南面有一排朝北的房屋,類(lèi)似于四合院的倒座,通常作為賓客、男仆居住,或書(shū)塾,或雜間,自此向前經(jīng)過(guò)二道門(mén)才進(jìn)到正院,院子里是很大的一棵桂花樹(shù)。過(guò)了院子是廳,廳又分正廳、餐廳和會(huì)客廳。二進(jìn)三進(jìn)之間也是一個(gè)很大的門(mén),相當(dāng)于四合院里垂花門(mén)的作用,是內(nèi)宅與外宅(前院)的分界線,這道門(mén)起屏障作用,保證內(nèi)宅的隱蔽性。從邊上可以上二樓。最后是一個(gè)竹園子。
“我母親是新時(shí)代婦女,上學(xué)校,學(xué)的是養(yǎng)蠶,就在院子里種了不少桑樹(shù),每年都盼著打甜桑葚吃。鄰居家的小孩也到院子里來(lái)玩,打下的桑葚不洗就吃,弄得一嘴紫色。”張敬淦離開(kāi)老家快60年,講起這些老房子里的童年還充滿(mǎn)著向往。
“從祖上開(kāi)始,這套祖宅就由長(zhǎng)房系統(tǒng)來(lái)管理,到我父親手里,他復(fù)旦畢業(yè)后到上海做中學(xué)教員,很長(zhǎng)有時(shí)間委托別人代管家業(yè)。”張敬淦說(shuō),可是一解放,問(wèn)題就來(lái)了,這么大的房產(chǎn)怎么定性,“1949年,我到北京工作,參加革命,要填表,家庭成分不知道怎么填,后來(lái)專(zhuān)門(mén)有人去老家調(diào)查,因?yàn)槲腋改府?dāng)時(shí)的工作都還有不低的薪水,結(jié)論是我們出租房屋和地租收入占我們家總收入的5%到6%,算不上地主,這套祖宅才逃過(guò)了被沒(méi)收充公的命運(yùn)。”“最后我家庭成分填的是自由職業(yè),個(gè)人成分是學(xué)生。”
來(lái)北京前,張敬淦在上海念書(shū),就住進(jìn)了石庫(kù)門(mén),只有暑假才會(huì)回老家,“簡(jiǎn)直是兩個(gè)世界”,張說(shuō),“上海那么擁擠,狹小,一回老家,大得不得了,甚至根本用不了這么多房子,居住對(duì)我們這一代中的很多人來(lái)說(shuō),都是這樣分裂的。”“房子和命運(yùn)一樣,都是被規(guī)制好的”,他說(shuō),讓他備感懷念的是有院子有竹園的老房子永遠(yuǎn)沒(méi)有辦法遷置上海,也沒(méi)有辦法遷置北京。
不光如此。當(dāng)他從上海到了北京之后,好的居住同樣是個(gè)奢侈的愿望,并且這個(gè)大城市也正在為他這樣的新進(jìn)人口的居住問(wèn)題頭疼不已。
被“擠爆”的四合院
丁艾家的四合院為什么要換地磚?就因?yàn)楸緛?lái)隔潮很好的家里到雨季滲水滲得厲害,查了一圈才弄明白是那個(gè)“氣眼”被堵住了,她說(shuō),“當(dāng)時(shí)四合院的住戶(hù)越擠越多,每家的人口也越來(lái)越多,就都借院子的后墻加蓋屋子,屋子的地基原本比院子高,他們要加,就要做一個(gè)和臺(tái)階一樣高的地基,這一來(lái),‘氣眼’就被堵在里面了”。
丁艾家的四合院在50年代成了大雜院,最多的時(shí)候,有五六十口人擠在這原本給一家人住的院子里。丁艾說(shuō),住在東廂四間房的一家三代人,奶奶、兒子、兒媳、還有6個(gè)小孩,“堵住‘氣眼’的房子就是他們家蓋的,因?yàn)樗拈g屋實(shí)在住不下了”。
丁艾的家可能還不算擁擠的。到80年代末北京危改試點(diǎn)工程開(kāi)始,一些四合院居住的擁擠程度,當(dāng)年參加危改工程的北京建筑設(shè)計(jì)研究院住宅設(shè)計(jì)研究所原主任、建筑師黃匯回憶說(shuō),“當(dāng)時(shí)城規(guī)控制建筑高度限四層,容積率限1。15,而拆遷小后倉(cāng)胡同,人口居住密度之高,以至于如果把可能建造的全部住宅都還給原住戶(hù),每戶(hù)平均也僅能得到46平方米,當(dāng)時(shí)一般職工分配住房的標(biāo)準(zhǔn)為平均每戶(hù)56平方米,而這些四合院住戶(hù)每戶(hù)的人口都在十來(lái)個(gè)人左右,你說(shuō)這個(gè)胡同里的四合院在漫長(zhǎng)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擠著多少人?”
丁艾說(shuō),和她家一樣,四合院的擁擠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閹状螖D進(jìn)居民的歷史時(shí)期,1949到1953年為第一次,當(dāng)時(shí)是大量的進(jìn)京軍隊(duì)及軍隊(duì)家屬、政府工作人員以及農(nóng)村土地革命逃亡出來(lái)的地主富農(nóng),還有就是災(zāi)荒與水荒中的難民。1957年“經(jīng)租”政策出來(lái)后,胡同內(nèi)的獨(dú)門(mén)獨(dú)院很多都變成大雜院,因?yàn)橄麥绶慨a(chǎn)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間自留房之外的房屋,給那些貧苦的無(wú)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房管局接收了所有私房,很多軍代表與工人階層住進(jìn)了胡同,四合院的人口壓力又陡然增加。
寧?kù)o而中國(guó)式的四合院生活被打破,不光是丁艾這些從胡同里長(zhǎng)大的人居住歲月中的疼痛,也是這個(gè)國(guó)家和城市發(fā)展中轉(zhuǎn)型的陣痛。更重要的還是發(fā)展中的問(wèn)題。張敬淦說(shuō),1953年中國(guó)進(jìn)入第一個(gè)五年計(jì)劃,“其實(shí)當(dāng)年計(jì)劃生育的壓力還不是很大,完全是由遷移人口帶來(lái)的。北京成立了新部委,每個(gè)部委下面成立的機(jī)構(gòu),都要從外地大批調(diào)集人才,引進(jìn)人才的條件首先是要解決居住問(wèn)題”。“就地蓋房已經(jīng)開(kāi)始,但畢竟需要一個(gè)周期,于是舊城的四合院就成了用人單位的一個(gè)不二選擇。”張敬淦就是這批最早調(diào)入北京的技術(shù)人員之一。他與同他一起從上海來(lái)北京的同事住在單位給的宿舍里,兩個(gè)人一間房,十二三平方米一間,就是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四合院,“這所四合院的門(mén)面是一個(gè)大當(dāng)鋪,我們住的是廂房,當(dāng)鋪叫‘永存當(dāng)’,我們當(dāng)時(shí)幾個(gè)人開(kāi)玩笑說(shuō),‘我們要被永存’了,這輩子出不去了”。
四合院的壓力在接下來(lái)的幾年不僅沒(méi)有減少,反而到了要被“擠爆”的程度。涌入北京的人口還在持續(xù)增長(zhǎng)。趙景昭說(shuō),建國(guó)以前,老北京城1350萬(wàn)平方米住宅住了不到100萬(wàn)人,現(xiàn)在一個(gè)區(qū)都要60萬(wàn)人。“從七八十年代以來(lái),黨中央、國(guó)務(wù)院和中央書(shū)記處,關(guān)于北京城市建設(shè)的方針和規(guī)劃曾經(jīng)做過(guò)6次書(shū)面的指示和批復(fù),其中對(duì)北京城市人口明確規(guī)定的就有兩次,最初規(guī)定市區(qū)人口控制在400萬(wàn)左右,但結(jié)果看,北京的每一次人口控制都失效了,為什么?”張敬淦說(shuō),“建國(guó)后,北京開(kāi)始在老城里搞工廠,準(zhǔn)備把它從消費(fèi)型的城市轉(zhuǎn)向生產(chǎn)型城市,各種工業(yè)項(xiàng)目不加選擇、不加限制地紛紛上馬。北京原有的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由于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階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減法并用,就是主要發(fā)展薄弱的產(chǎn)業(yè),同時(shí)并未壓縮應(yīng)當(dāng)壓縮的產(chǎn)業(yè),所以工業(yè)規(guī)模不但沒(méi)有控制住,甚至一直保持著兩位數(shù)的增長(zhǎng),而且重工業(yè)在繼續(xù)發(fā)展。北京過(guò)去搞老三件——自行車(chē)、縫紉機(jī)、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彩電、冰箱、洗衣機(jī)”,“關(guān)鍵是,人來(lái)了,住房從哪里來(lái)?”
在張敬淦看來(lái),許多城市犯了這種發(fā)展中的通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急于發(fā)展,引起諸多后遺癥。中國(guó)人的居住成為首當(dāng)其沖的對(duì)象。他說(shuō),四合院見(jiàn)縫插針建小工廠,并開(kāi)始安置更多居民進(jìn)入,有些房管所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現(xiàn)在看到的青磚紅磚,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時(shí)搭蓋起來(lái)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內(nèi)的問(wèn)題就是市政欠債越來(lái)越多,電力電信與上水基本解決,但下水還是使用著清末與民國(guó)的設(shè)施,沒(méi)有下水系統(tǒng),都用滲井,就是挖一個(gè)幾米深的洞,填上泥沙,靠天然的地滲來(lái)排生活污水,在建造新的下水系統(tǒng)時(shí)我們統(tǒng)計(jì)過(guò),全北京四合院有27000口滲井還在使用。”
這個(gè)時(shí)候的四合院顯然就不再是庭院深深的棲居之地,早已成了“無(wú)風(fēng)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雜院了。丁艾說(shuō),她家的五口人,幾年間孩子都長(zhǎng)大了,1976年知青返城,找到工作的有了單位分的房子,沒(méi)有工作的就回到院子里來(lái),也到了該結(jié)婚的年齡,沒(méi)房怎么辦?就再充分利用四合院院子的空間,把院子里種的丁香、海棠拔了,在父母的房子旁邊加蓋房子。80年代燒煤氣,紛紛搭廚房。她說(shuō),她們家還算好的,“更多的四合院,里面又成了一個(gè)小胡同了”。
四合院所講究的日曬、采光于是被解決人們基礎(chǔ)住房擠得蕩然無(wú)存。一家4口在這樣的雜院里住了30年的北京人謝其章說(shuō),“我們當(dāng)年住在一個(gè)大雜院的頂旮旯,出門(mén)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墻,于是每天上午9點(diǎn)到11點(diǎn)之間,是我惟一能看到陽(yáng)光的時(shí)辰,那陽(yáng)光被山墻和廚房擋著,遙遙地投在我的白墻上,只有一線,想想,真是30年如白駒過(guò)隙。”謝告訴記者,“從這間大雜院搬到新居,雖然也只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口子迫不及待連續(xù)7個(gè)晚上把墻刷個(gè)大白,還趕了個(gè)新潮從西單商場(chǎng)買(mǎi)的地面鋪的地板革,8塊錢(qián)1米,“新房子也沒(méi)法南北通風(fēng),朝向也不太好,但好歹算是個(gè)新家了”。
丁艾說(shuō),“原來(lái)每家四合院種的石榴、丁香這些植物和大棗樹(shù)差不多都所剩無(wú)幾了,現(xiàn)在大雜院里最常見(jiàn)的香椿樹(shù)、大楊樹(shù)和核桃樹(shù)都是80年代‘號(hào)召植樹(shù)’運(yùn)動(dòng)中引進(jìn)的樹(shù)種,就這幾種,沒(méi)什么可選擇的”。丁艾家東屋門(mén)口的4棵楊樹(shù)樹(shù)干已經(jīng)空了,“搖搖欲墜,怕風(fēng)一刮倒了砸壞屋子,前年給園林局打了個(gè)電話(huà),他們派人來(lái)把樹(shù)干鋸下了,拿大鐵絲綁了綁。”丁艾帶著夾雜著幸運(yùn)的惋惜口吻說(shuō),“不過(guò),現(xiàn)在能一家人住一個(gè)院子,院子里還有樹(shù)已經(jīng)不錯(cuò)了。”
“失去的”居住
在北京第一次“住房難”出現(xiàn)和幾乎北京舊城的所有四合院“添丁增口”的同時(shí),北京也進(jìn)入了一次住宅建設(shè)高歌猛進(jìn)的時(shí)代。“政府的確不斷在想辦法,增加居住房供應(yīng)量。”林晨說(shuō),“從1949~1978年的30年,北京新建住宅面積2953。053萬(wàn)平方米,超過(guò)了舊城原有住宅面積的兩倍以上。”
盡管這里面大量的住宅帶著濃厚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味道,像1950年左右北京加急興建的一批磚木結(jié)構(gòu)平房住宅,坐北朝南,成行排列,被人們稱(chēng)為“兵營(yíng)式”。趙景昭說(shuō),“1960年公社化運(yùn)動(dòng),北京在東城、西城、崇文設(shè)計(jì)建造了三棟‘公社大樓’,以二室戶(hù)為主,每戶(hù)有衛(wèi)生間,沒(méi)有廚房,因?yàn)闃窍掠泄彩程茫袃核突顒?dòng)用房,‘公社化’集體食堂解散,結(jié)束了住宅設(shè)計(jì)沒(méi)有廚房的歷史,對(duì)原來(lái)所有沒(méi)有廚房的住宅進(jìn)行了一次全盤(pán)改造。1965年學(xué)大慶‘干打壘’、‘先生產(chǎn)后生活’,設(shè)計(jì)了31套‘簡(jiǎn)易樓’圖紙,蓋了一大批簡(jiǎn)易樓,簡(jiǎn)易門(mén)窗,無(wú)紗窗,無(wú)衛(wèi)生間,不用磚砌墻,用木板中間加土,再夯,這樣能省不少錢(qián)。于是蓋了一批‘窄小低薄’的樓房”。但政府為此支付了大量國(guó)家財(cái)政,廉價(jià)而簡(jiǎn)易的住房也讓政府背上了極為沉重的“住房包袱”。這筆錢(qián)龐大到無(wú)法計(jì)算,僅根據(jù)1992年統(tǒng)計(jì),全國(guó)12億平方米的公房,即使按每平方米120元的建筑價(jià)格計(jì)算,也有上千億的資金在里面。
“‘簡(jiǎn)易樓’、‘筒子樓’同樣是當(dāng)時(shí)政府在錢(qián)袋緊張情況下的無(wú)奈之舉。”張敬淦認(rèn)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層高”理所當(dāng)然成為中國(guó)后期住宅建設(shè)犧牲掉的品質(zhì)之一。
“1978年,鄧小平視察前三門(mén)住宅樓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設(shè)計(jì)要考慮住戶(hù)方便,同時(shí)提出了要‘降低住房造價(jià)’的要求。”趙景昭說(shuō),當(dāng)時(shí)絕大多數(shù)建設(shè)者的意見(jiàn)是,在不增加投資或適當(dāng)減少投資的條件下,以適當(dāng)降低層高來(lái)擴(kuò)大使用面積,“我們傳統(tǒng)民居的層高一般都在4米以上,因?yàn)橹惺阶≌慕ㄔO(shè)者普遍認(rèn)為,房屋層高越高,室內(nèi)高低處溫度的溫差越大,空氣對(duì)流越好,人體感覺(jué)越舒適,當(dāng)年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規(guī)定的層高是2。9米”。“后來(lái)經(jīng)過(guò)論證,認(rèn)為保持每戶(hù)投資不增加的前提下,層高降低20厘米,每戶(hù)可增加3個(gè)平方米,這樣定下來(lái)之后,北京將多層住宅的建筑面積標(biāo)準(zhǔn)由每戶(hù)53平方米提高到了56平方米左右。”“北京因?yàn)榫暥鹊停救照赵?2月22日冬至前后只有26度30分,所以早期蘇聯(lián)專(zhuān)家推薦的四層住宅單元,層高上定為3。3米,是考慮到房間日照時(shí)間采光效果的,但大幅降低層高,又增加住宅密度后,許多居民樓的采光都受到影響。”
如何重回到在“三間五進(jìn)”的大院子里看四季變遷?趙說(shuō),“房子越蓋越高,建筑材料從磚混到大模到輕體框架結(jié)構(gòu)。以前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木結(jié)構(gòu)房子,建造時(shí)要選東北的紅松黃松,特別是椽檁講究的都要使老黃松,太陽(yáng)一曬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磚對(duì)縫’,就是把老磚對(duì)老磚磨,砌的時(shí)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漿水滲進(jìn)去。”“至少現(xiàn)在,多數(shù)人居住的房子是不會(huì)這么去蓋了。”